
InVisor科研新闻 |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核辐射的危害无人可以避免……
2021年5月7日
技术转移——高校的新型科研之路(@帝国理工学院)
2021年5月11日你心目中的「文学的天花板」是什么?听双雪涛朗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有一说一,InVisor芳老师首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翁)是19世纪的俄国作家,他不仅继承了前几个世纪诸如“人文主义”、“启蒙理性”的文明成果,而且也用近乎神性的洞察力预见了20世纪乃至今天乃至未来的人类处境。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陀翁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其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艺术技巧也是致臻成熟,皆属世界上第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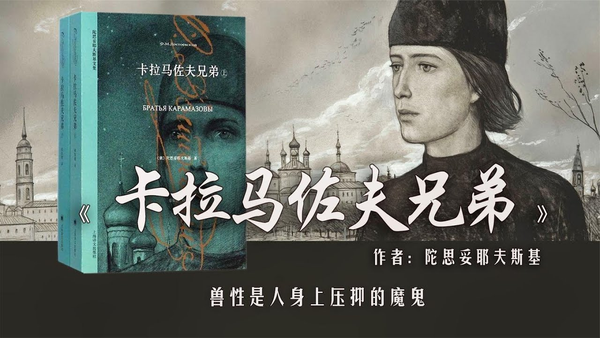
(对文学研究等科研课题感兴趣的同学,欢迎戳戳InVisor芳老师的客服微信: invisor003)
一、作家作品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与苦难、贫困、疾病相伴。其父是一个医生,工作的医院地处莫斯科的荒郊野岭,周围是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儿院,于是他从小就经常观察这些穷人、病人并与他们交谈。
青年时期,陀翁因参与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被定为死罪,在临刑前几分钟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惊心动魄的体验与西伯利亚的苦役经历使得陀翁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后来又因赌博以及赡养家人的负担,陀翁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此外,陀翁还一生患有癫痫病,身心一直承受很大痛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翁的最后一部小说,也被认为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遗憾的是,只完成上部,下部还没来得及写作家就因肺病逝世了。尽管如此,上部所蕴含的光辉就已经足够我们用几个世纪去消化了。
作品背景设置于十九世纪的一个“偶合”家庭,父亲老卡拉马佐夫是一个坏事做尽、没有信仰的酒色之徒;老大德米特里激动狂躁,追求声色犬马又时时良心不安;老二伊万以无神论者自居,坚持“理性主义”,但是又常常莫名地感到痛苦;老三阿辽沙是一个修士,但他没有躲在修道院内而是奔走于世间与世人一起体会痛苦,是悲剧中希望的化身;仆人斯乜尔加科夫其实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他崇拜伊万,最终也在伊万“百事可为”的信条下走向毁灭。
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弑父”展开,通过描写几兄弟在这场弑父案中的表现,建立起了一个个上帝与理性、道德与罪恶、真理与虚无的角斗场,无所不包地摹写了人类的灵魂。

二、思想内涵:上帝到底存不存在?
19世纪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欧洲启蒙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涌入,社会上下都浸入一种怀疑论中——上帝存在吗?宗教信仰问题几乎成为了当时俄国社会最亟待解决的危机。陀翁也深陷这一巨大的悖论之中: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有恶呢?这也成为了这部作品的核心话题。
在《反叛》一章中,当伊万论及人类的作恶是如何伤害孩子的时候,阿辽沙惊恐万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惨绝人寰的恶呢?就算成年人是偷吃了禁果的罪人,那与无辜的孩子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位大将军放狗将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在他母亲面前活活给撕咬至死。当伊万问阿辽沙大将军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时,善良的阿辽沙脱口而出“枪毙!”这位修士无法解释这一切,也无法拯救那些孩子。那么如果至善上帝真的存在,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一切呢?
Q:但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就能获得幸福吗?
小说中是斯乜尔加科夫杀死了老卡拉马佐夫,但罪魁祸首是伊万的理性主义——他否定上帝的存在,认为“百事可行”,因为没有上帝,也就没有善恶,那么也就没有惩罚,一切归于虚无。斯乜尔加科夫正是听了伊万的这一番论调杀了人。如果这套说辞是真理,那么“弑父”成功之后,这两个无神论者应该能够获得幸福:伊万可以得到父亲的遗产,或者斯乜尔加科夫可以实现自己开餐馆的愿望。但是真正的结果呢?伊万疯了,斯乜尔加科夫也自杀了。陀翁借此表达了对人的自由的质疑。西欧理性主义赶走了上帝,没有上帝,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真理,每个人都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但是人类心灵固有的恶使得自由既可以导向善,也可以导向恶 。
无论老卡拉马佐夫是多么的罪不可恕,“弑父”这一行为总归违背了自然法则。伊万所遵奉的“理性”源自人,可如若没有更高的法则来约束人类,纯粹的“理性”只会造成社会的失序。所以陀翁说,如果获得真理的代价是这样,那么他“宁愿与基督而不是真理在一起”。陀翁跳脱理性逻辑论证的思维,通过“弑父”案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 。
Q:那么上帝当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当陀翁看到当时的罪恶、苦难,以及人与人之间日益封闭的相处方式时,他觉得一切社会制度都是无效的,唯有道德的重建才能改变这样的隔绝,而这一任务应当交予上帝来完成。在陀翁那里,上帝确实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但不是一个要求信众愚忠的人格化暴君,而是普遍真理、道德法则的代表。上帝不掌控整个世界秩序,不是奇迹的施行者,而是作为“真善美”的道德追求存于每一个具体的心灵之中——就像佐西马神父和阿辽沙所践行的那样。
其实,除了罪恶和苦难,作品也处处都隐含着希望——德米特里在法庭上的认罪与牺牲、宗教大法官在耶稣默默亲吻自己后的颤抖,甚至伊万的发疯、斯乜尔加科夫的自杀,都是人类的向善之心战胜了罪恶。陀翁写遍了恶,最后却通过阿辽沙在伊柳沙葬礼上的演说,传达了那些感人的话语:“或许将来我们甚至会变得凶恶,甚至不能悬崖勒马而干出丑行坏事,或许会拿别人的眼泪开心。刚才郭立亚说他愿为全人类献身,或许将来我们会嘲笑那些像他这样说话的人,或许我们会恶毒地挖苦他们。不管我们会变得多么狠毒——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但只要我们回忆起我们曾为伊柳沙送葬,在他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爱他,此刻在这块大石头旁边,我们曾这样聚在一起友好交谈,——那么,即便是我们中间最狠毒、最好挖苦的人(如果我们变成那样的话),他在自己心里毕竟不敢嘲笑自己此时此刻曾经那么善良、那么仁爱!不但如此,也许恰恰只有这段回忆能制止他作大恶、闯大祸,那时他可能回心转意,可能会说:‘是的,当初我曾经那么善良、勇敢和正直。’”
三、艺术技巧:复调
“复调”是陀翁小说的根本艺术特征。这一理论由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又称“多声部”,顾名思义,就是“不同的声音各自唱着同一个主题” 。其理论基础是“对白”,陀翁和巴赫金认为人的生活在对白中产生,“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没有面向别人的相互关系,自我意识就不可能产生。
陀翁之前的传统小说都属于“独白小说” ,作者主导人物,人物只是作者统一意识的传声筒,两者之间不是平等的。这样也许会导致创作不自由也不真实,有时作者可能会为了抒发自己的立场而改变故事应有的逻辑结果。
陀翁开创了“全面对白小说” ,他笔下都是具有主体性的独立人格,而不是作者控制的扯线木偶,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作者之间都处于平等对话的关系,每个人物都自成一套思想系统并不断为之与别人辩论,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则是客体。在陀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物怎样存在于世界,而是世界怎样存在于人物的意识。陀翁敲击每一个灵魂的多块碎片,使之发出不同的声音,再整合成整体 。
这样的艺术视角十分利于灵魂的深层剖析及事物本质的揭示,比如伊万与斯乜尔加科夫的对话,表面虚饰又充满暗示,可以看出两人都想要否认上帝却又存有疑虑。
甚至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也包含着与别人的对白或是两种人格的对白,比如德米特里花光了卡捷琳娜的钱后,既自责自己成了“贼”,又向别人辩解自己不是贼,自己会还的,这层层对白在德米特里一个人物的头脑中展开,就显示了他思想的重重矛盾;再如伊万和幻觉中的自己对话,体现了他灵魂深处因否定上帝而产生的痛苦挣扎。每一个主人公都是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他们与周围的环境不断对话,不停地自我剖析,这样的心理刻画是动态的,作家根据人物的观念逻辑来推演出其讲话的内容,但这一内容却并不一定是作者的主张,所以这种人物不是明晰、静态的社会典型,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作者本人也不能预先看到他笔下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就给予了艺术创造以无限可能。
不仅仅人物的微观心理,小说的结构也是“多声部”组成。比如,关于“上帝是否存在”,既有伊万的高谈阔论,也有佐西马神父叙述他为何笃信上帝的长篇自白。这也体现了陀翁创作时的平等对话原则,他并不给统一的处方,只负责展现各种观念,将分辨抉择的权利留给读者。其实这也是陀翁本人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他不像提出“合理利己主义”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托尔斯泰主义”的列夫·托尔斯泰一样,以人民的导师自居,而是与所有普通人一样,是一个痛苦的诘难者。
四、其他影响
陀翁的作品对20世纪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领域不用说,名家巨擘如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卡夫卡、纪德、加缪等深受其启发,文学思潮如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奉其为鼻祖;哲学领域则有东正教哲学、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也是直接受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启发而提出;甚至还有心理学领域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死本能”等。总言之,陀翁是当之无愧的“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加缪曾说:“还没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赋予荒诞的世界以如此令人亲切和痛苦的魔力。”《卡拉马佐夫兄弟》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
荣如德在译后记中写道:“极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俄罗斯。” 看完这本书,毫不夸张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全世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InVisor学术科研!喜欢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双击屏幕解锁快捷功能~
如果大家对于「SCI/SSCI期刊论文发表」「SCOPUS、CPCI/EI会议论文发表」「名校科研助理申请」等科研背景提升项目有任何想法的话,十分欢迎大家戳一戳InVisor芳老师(一般人芳老师是不会告诉ta客服微信滴:invisor003,记得备注“学术科研”哈~~~)❤️


